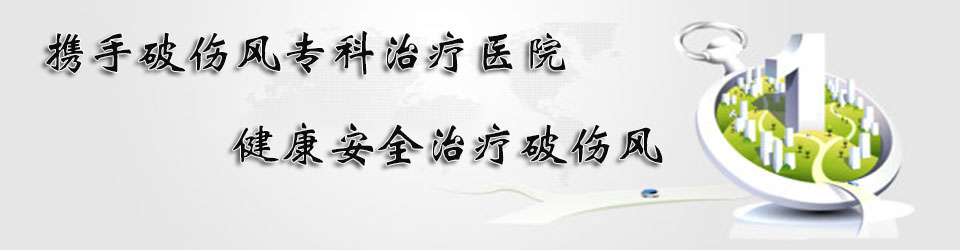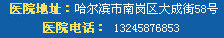静静地做自己,让世界发现你。
站在小镇街头向东眺望,远远可以看见一座高高的山峰突兀东北方,笔架似的山尖“鹤立”群峰之中,那就是圣垛山。听说那是内乡第一峰,山上是未被开发的原生态,山中有“唐王寨”,山顶有祖师庙等等,一次次心动,总有一些攀登过的人泼来一瓢瓢冷水,什么山势险峻、上山无路,什么无导游带领不可上,什么山中有野猪毒蛇等等,诸如此类阻止的缘由,可喜欢爬山的人心里怀有一个坚定信念,再高再陡的山也挡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,清明节前夕,约起几位朋友踏上了去圣垛山的游程。
圣垛山位于马山口镇关帝坪村北,路程不算远,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就来到了山下的小村庄,小山村叫黑虎庙,村名的来历没有考究,村里人大都搬迁山外,留守的寥寥无几,很难找个向导。问问村头的一位大姐“上山咋走?”答曰:很少人上山,哪有路!只有偶尔进山弄山货的人踩下几条影影绰绰的“蹊径”。她指了指大概“路线”,我们背起干粮和水,拄着拐杖登山了。
这的确是座少有人攀爬的山,山路羊肠,隐没在杂草荆棘中,山脚是低矮的山坡,不算陡峭,可一时很难找到入口,绕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条模模糊糊的小路。大家来了精神,拨草寻路,向着主峰方向迂回前进。山脚植被较好,桦栎树是主要树种,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杂树,荆棘、杂草已经返青,树木开始吐绿,满目嫩绿,山林中些许山桃花、山梨花、紫荆花和无名小花艳艳盛开,特别的耀眼,“野芳发而幽香”,走在其中,使人感觉到了春天的气息。同伴们劲头十足,几个女同胞也不甘落后,大家时不时边走边吼几声,前者呼,后者应,声音在山谷回荡,惊起了路边的蓬间雀,叽叽喳喳飞走了,别有一番意趣。
随着海拔高度的增高,山腰的植被发生着变化,生物学家研究表明,海拔每升高米气温要降低6摄氏度左右,所以半山腰的草木刚开始萌芽,只有零零星星盛开的迎春花点缀山间。山势逐渐陡峭起来,小路在乱石悬崖中时隐时现,稍不留心就会“误入歧途”。我们边走边探路,还得留心脚下的坎坎坷坷。
常言道“看山跑死马”,真不瞎说,明明是一座山,可一山走过一山拦,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,忽而隐没在荆棘丛中,忽而又消失在乱石堆里,忽而把我们引向深谷,忽而又把我们导向山棱,好不容易转过一道山梁,猛然间又有一堵峭壁立于眼前,“千岩万转路不定”,走着走着“陷入深谷”,竟看不见主峰了!同伴们一个个呼哧呼哧喘着粗气,腿开始打颤,气力有些不支,体力好的走在前面,体力差的开始走走停停落在后面,几个女同胞开始打退堂鼓了。走在前面的同伴不住地在鼓劲:“走一半了”“快到山顶了”,明知是“忽悠”,还得往前走。
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,“会当临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我们相互鼓励着,手脚并用,手揪着路旁的枝蔓,脚踩着杂乱的顽石,慢慢地挪动着脚步向上爬去,恨不得“胁下生双翼,直飞到山顶”。
本人属于那种不合群的玩伴,用同伴的话说“我们旅游是看风景,完成的是过程;你看风景,要拍照片,还要考察沿途的人文”,人生有如登山,登顶固然重要,但沿途也应该慢下来,不时停下脚步,看看沿途的风景,享受攀登过程。我一边走,一边用猎奇的目光搜索着沿途的奇观,并不时按动相机快门,定格山间美景。半山腰植物的生存条件大不如山下,山间乱石遍布,奇石林立,据说圣垛山山体为燕山期花岗岩,形成距今2亿年,有的植物生长在悬崖峭壁上,有的生长在乱石堆中,甚至石缝中,面对这些夹缝生存的植物,我由衷的敬佩,大自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!
就这样走走停停,蓦然抬头,一段石寨墙赫然眼前,石寨依山就势用石头垒成,已经被山洪冲涮得残缺不全,仅剩几节残垣断墙,但依稀可以看到其重要的地位。石寨向上是一段陡峭的木梯子,需小心攀缘而上,这是头道寨。往上又行半里多,是二道寨,这里离山顶不远,更是要塞之地,只见一个门洞,仅容一人通过,一夫挡关,万夫莫开,再往上还有三道寨。
据说原来寨里住有人家,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搬至山下,现在寨内还留有石碾、石磨、石磙、石槽、磨刀石和残存房屋的痕迹,不敢想象那些人们当时是咋在这里艰难生存下来。原以为这就是唐王寨,可上山后问问知根底的人说,这几道寨是元朝时荆州一股叛匪潜逃这里修建的,并非唐王寨。
抬头向上看,那直插云霄的金顶近在咫尺,山垭上传来几个前行同伴的呼叫,“面条煮好了,赶紧上来啊”,本以为是戏言,荒郊野岭、高山之巅,哪有这等好事!我们几个颤颤巍巍爬上山垭,真的飘来饭香,一口柴锅里正“咕嘟”“咕嘟”煮着面条,其中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笑脸相迎,同伴介绍说:年轻人是守山的,老人叫樊宏烈,听到老人的名字,我顿时愕然:这就是樊宏烈啊,他可是马山口的名人,搞慈善、办学堂,轰轰烈烈,早有所闻,只是没想到在这样的地方结识了,有缘人“天涯何处不相逢”,樊哥说:这就是缘分。一碗干酸菜面条,填饱了辘辘饥肠,也抚慰了一身疲惫,高山一碗面胜似餐馆一顿山珍海味!樊哥一分钱不要,还不住地说“太简单”了,我等已感激不尽!
吃了饭,樊哥带领我们一鼓作气爬上山顶。经过5个多小时艰难挣扎,我们终于站在圣垛山顶了,山登绝顶我为峰,站立山顶一种成就感、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环视四周,周围群山起伏连绵,错落有致,像一层又一层的海浪翻涌而来,远处的山峰就像是站在对面,仿佛伸手可及,东边的云露山、西边的麦子山、北边的金鸡峰都矮了很多;圣垛山主峰三峰相连,挺拔峻秀,形似笔架,其中南边的山峰和向下的峰岭连起来形似一只睡狮,也有人说像一只卧虎,为圣垛山增添几分神秘。
俯视山下,有“小天下”之感,静卧在群山怀抱之中的村庄清晰可见,连接村庄的村村通公路向远方蜿蜒游弋而去,白墙蓝瓦,烟雾缭绕,好一幅人间仙境图。明代诗人李衮攀登此山写诗:“圣垛山名自昔闻,耸然不与众峰群。深藏翠壑千层雪,高挂晴天一片云。原始到今如削玉,巨灵何处可惮斤。我来登眺浑忘倦,遮莫西林下夕曛。”圣垛山之美,名不虚传。
山顶的植被与山脚相比,判若两季,这里的草木依然沉睡在冬季里,树木光秃秃的还没萌芽,几只乌鸦在树林里呱呱地叫着,一派萧瑟和冷清,若不是山头含苞欲放的迎春花提醒,真以为走在冬日里。
传说祖师爷曾在这儿栖息停留,明朝永乐年间人们就在山顶建一祖师庙,供奉着真武祖师,历经岁月风雨和时代变迁,庙宇多次被毁,又多次修缮,至今金顶仍有一座小庙,虽然山高路远,人迹罕至,但祖师爷依然高居山顶,享受着信徒的尊崇膜拜,观赏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庇护着一方生灵。
据说唐朝初年,秦王李世民,迫于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追杀,带兵逃至这里,在此修筑山寨,屯驻兵马;唐中宗李显也到这里避过难。明朝末年唐王朱聿键曾驻此屯兵筑寨,留下了“唐王寨”。“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。”
圣垛山海拔米,是伏牛山脉中名山之一,自古有“一方圣概”之美誉;也是一座宝山,山上有山药、天麻、朱苓、黄精、金柴、蜂糖等名贵中药,是一个天然药库,所以马山口自古就是中原药材聚散地之一;圣垛山植被覆盖率高,花草树木种类繁多,名花奇树颇丰,就拿枫树来说吧,有三角枫,五角枫、七角枫、八角枫、九角枫等,尤其是四月,杜鹃花开满山坡,争芳斗艳,鸟语花香;山中还有各种珍奇动物,时常有野猪、野羊、野鸡、野兔出没,不少是珍奇的生物标本和活化石,备受生物学家青睐。因为原始,所以神秘,这里留有很多诡异的地名,如“金灯崖”、“鳖爬崖”、“拱肚儿崖”、“金钗崖”等,一个地名都是一个故事,值得去探秘研究。
高处不胜寒,金顶纵有风情万种,我等也不愿在此久留,纷纷要求下山。因为山况不熟,我们只有沿原路返回。俗话说,上山容易下山难。原路本来就是乱石杂草丛中的一条便道,同伴们一身疲惫,稍不留心踩到树叶或石板上的沙粒,就会摔倒,咬着牙用拐杖支撑着深一脚浅一脚向下滑行,一路上还是摔了不少跤。就这样,又折腾了三个多小时,才回到山下村子。
回望圣垛山,它依然不温不怒挺立在那里!忽然想起仓央嘉措的诗句“你见,或者不见我,我就在那里,不悲不喜;你念,或者不念我,情就在那里,不来不去。……”我羡慕圣垛山的博大胸怀,独居苍穹之一隅,即使被世人遗忘和冷落,依然傲然挺立、不卑不亢,纵然有万种风情也不张扬,坐看云卷云舒风霜雨雪,笑傲草木盛衰花开花落……
下山后,不顾疲惫劳顿,我们直接去了圣垛法云寺。有圣山必有名寺。古人把圣垛山看作圣山,佛教传入中国后,佛教人士就来到这里寻觅道场。圣垛山南麓的一处山坳,山清水秀、云遮雾障、清幽雅静,被僧人相中,不知道他们经过多少年的辛苦努力,终于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,并美其名曰“圣垛法云寺”。根据塔碑记载:法云寺建于明代以前,明、清时期重修过,明、清时期佛事、香火最为兴盛,清末至民国开始衰败;民国后期,寺院全毁,仅剩大小佛塔10多座;因年久失修,五十年代中期塔群倒塌毁坏,再加上文革时期的“破四旧”,现仅存一塔。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”,宏大的法云寺、济济一堂的僧侣、悠扬的暮鼓晨钟声和纷至沓来的香客,都被时代的飓风吹走了,仅存一座摇摇欲坠的古塔……
来到古塔脚下,举目仰望。古塔拔地而起,古朴雄浑、昂首挺立,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多年的风雨沧桑……伫立塔前,我仿佛读懂了沧桑之下亘古不变的真理,正如明代诗人杨慎诗云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”,在永恒的时空中,每个人都是时间的过客,看谈一切,淡定而从容,珍惜当下,好好生活。
曹万琪:男,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赤眉镇人,本科学历,中学高级教师,南阳市作协、影协会员,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,内乡作协副秘书长,内乡影协副秘书长,本人喜山乐水,喜欢摄影,爱好文学,偶有拙作发表于报刊、网络。出版有散文集《我自故乡来》。
作家文刊《青春在》(Youthexists)发布
本文摄影:曹万琪
◆◆◆
原创授权
原创首发,一稿一投,文责自负,字以上,作者简介、帅照同发ID:gh_fef7d邮箱:qq.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hl/39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