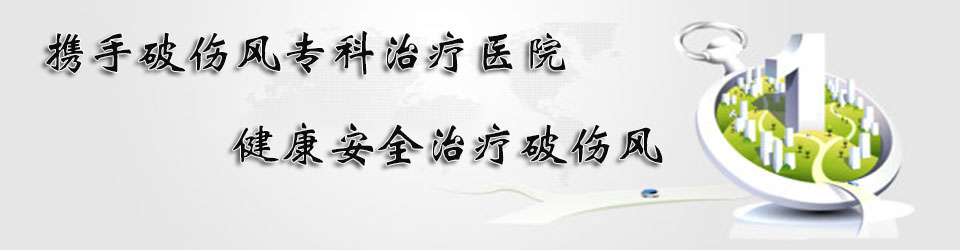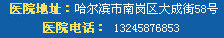当八百里伏牛山,自西浩荡到达栾川境内时,这里便以崇山峻岭、风景秀丽闻名。唐以前,老君山原名景室山。太宗李世民寻根问祖,与道家元圣李耳联宗,听闻老子曾在此修炼,就更名老君山。山上建有老君庙,历代文人墨客络绎拜谒,留下了众多华章和遗迹。
山因人而盛,人因山更名。比如武陵春人的桃花源,如果没有陶渊明,谁会知道那个与世隔绝几代人的犄角旮旯地儿呢。再比如岳阳楼,如果没有范仲淹的妙笔生花,恐怕也没有今天的闻名遐迩。所以,老君山是天地造化的杰作。看见他了。他站在山口,长须冉冉。他一指向天,一手执经。身披一领锦袍,在日光下熠熠生辉,是世人膜拜圣人的颜色。看见他了!他化为了一座山脉。一袭青袍的他,不嗔不怒,就站在那片氤氲的霞光里。这一站,是亿万年的岁月流转,是亿万年的草木枯荣。云,已不是昨天的云;风,也不是那来日的风,可山,还是这座山——唐之前,山清水秀;唐之后,地杰人灵。
窃以为,山水之妙,妙在使人心神松弛,心静身安。而老君山——这座道家名山,便有这样的魔力。远远地,就瞧见了那脉隆起的青绿,刚刚靠近,呼吸倏地缓了,脚步却轻快起来,身心像暖风里的柳条,慢慢舒展着。
歌里说“阿里山的小伙,壮如山”,我眼中的老君山,沉稳俊逸如隐者。人称陶渊明为“隐逸者之宗”,相较老子而言,绝对是“小巫见大巫”。近两百首的田园诗词,足以勾连陶渊明的生活轨迹。而老子骑青牛、过函谷,留下了五千真言后,就藏匿龙形,融于茫茫山水间,成就了千古流传的历史传说。亦真亦幻,正史野史,无不让人神往而浮想联翩。
走,让我们拾阶而上,去探寻圣人的足迹,感悟道之所在吧。
有人说,老子隐匿老君山,绝非信马由缰的邂逅。他曾任周“守藏室史”,饱读经传,这片山水之秀,恐怕早已萦记于心,出关后,他把这里当作理想的隐逸之所是多么的合情合理啊。可究竟是什么,羁绊迂回了老子的脚步呢?置身老君山,我在寻找着答案。
是那幽谷鸟鸣吧。初春的树冠还未丰盈,鸟雀的身形随处可觅。遇见来人,胆子大的,站在枝头,啾啾几声,似乎在说:欢迎啊,你是谁?胆儿小的,刚见到人影,翅膀便一展,嗖的没影儿了。可一会儿,它便在枝头等着你等着你欣赏春暖花开。这些精灵,喧而不闹,反而衬得山更加幽深,不是有诗句云“鸟鸣山更幽”吗?
是那“滑脱峰林”吧。也许,那里隐藏着天地造化的密码。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。”一块块岩石,经过风雨雷电乃至宇宙的揉搓,生生灭灭,高了,矮了,堆叠成今天的模样,似野马扬鬃,像群龙戏水,像刀锋林立……在世人眼里,它们是山。在圣人眼里,它们是什么呢?
是那山泉吗?山高林密绝人迹,春泉淙淙自在流。珍珠滩里潺湲不绝的泉水,看不见源头,却瞧得见身形。低洼处,它们聚成了潭,清澈如斯;高峻处,它们挂而成瀑,溅珠碎玉;平缓处,净洁如练。走着走着,看不见了,又冷不忒儿,就出现在眼前,被野花翠竹当作镜子,是小鱼儿小虾儿游戏的天堂。最妙时,是阳光斜射下来,丝丝缕缕犹如斑斓的锦缎。最好是夜晚,最好有片蛙鸣,月光和着泉的清音,合奏着春夜之歌,让生灵万物一起感悟“上善若水”的奇妙。
应该是那片云海吧。当杜甫发出“荡胸生层云,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喟叹时,一定是被雄立在云海中的山峰震撼了。我们的诗圣,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,云在他眼里,是虚无的。对,云是虚无的,却是那样的幽深莫测,它隐藏了山峰的锐利,削减了太阳的光芒,混混沌沌,同于尘俗。它们无形无迹,似乎不存在,似乎又包罗万象……这不是道,是什么呢?不知老子的“道冲,而用之或不盈。渊兮,似万物之宗;湛兮,似或存”是否因观云而得?
举头红日近,俯首白云低。这样想着,峰顶的我,合拢手掌,想捕捉一缕云,问个明白。似乎,云在我掌心流动,似乎,云又在千里之外……阵风吹来,心头萌生出两句诗:已得好水千山绿,且放白云归故乡。我想我,找到了答案。END
作者
杨亚丽
编辑
崔闪
审发
吴楠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#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zz/76.html